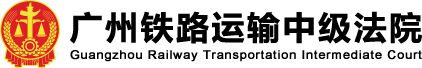“10%”一次道德与法律的浪漫牵手
 ?
?
广州市公安局起草的《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规定 “对拾金不昧的个人,可按拾获财物价值的百分之十的金额给予奖励”,经媒体报道并放大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网络争议话题,争论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举双手双脚赞同者有之,说风凉话叹息“人心不古,拾金不昧变味了”的亦有之。笔者作为一法律从业人,生怕这场火热的关注惊散这场道德与法律的美丽约会,几句撮合之言望他们牵手成功。
“对遗失物拾得者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或酬金”实际上是物权法范畴的法律问题,不仅是现代的也是历史的。我国历史上对于“拾遗”的态度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古代典籍中可考的最古老的关于“遗失物”的记载《左传?昭公七年》:“周文王之法,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意思是文王和各部族首领达成的协议,约定对于走失的牛马、奴婢不占为己有,应该主动归还失主。这是《物权法》第109条“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在法律中最早渊源。《易经》中有关于“迷逋复归”的筮辞。春秋战国时期,更是规定“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即拾遗者将面临刖刑──砍掉一只脚。到了唐朝规定捡到东西满五日不交公以“亡失罪论”,宋代出现了招领公告制度,元朝仍然“拾遗近盗”,但确立了支付保管费用的原则(头匹有主识认者,征还已有草料价钱,然后给主)。这是《物权法》第112条“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在中国法律史上的最早形式。
当历史的指针指向1398年的时候,遗失物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革。明朝《大明律?户律?钱债?得遗失物》篇规定:“凡得遗失之物,限五日内送官。官物还官,私物召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给还失物人。如三十日内,无人识认者,全给。限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赃论,私物减二等,其物一半入官,一半给主。” 后世清律、民国的物权编与此基本一致。大明律就遗失物拾得制度设定了几个规则:1、拾得人附条件取得所有权;2、拾得人有权要求遗失人支付报酬。历史竟然有如此的凑巧,这竟然与欧洲日耳曼法的规则不谋而合。直到今天,不同意见的法学专家、普通民众还在为遗失物是否适用拾得人取得所有权主义和获得10%报酬而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600多年前两个不同文化、不同法律传统的地域就这个问题就基本上达成了默契。在欧洲,不管法国民法还是德国民法都毫无例外地赋予了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和附条件取得所有权的权利,在英美法中,失主认领遗失物时,拾得人都有权要求遗失人支付一定的报酬。这个“一定”是多少呢,我国台湾地区为30%,德国为5%-3%,日本为5%-20%等标准。
当今天广州出台奖励10%的规定仍然引发大家的争执,有人“高屋建瓴”地批评“奖励是对道德的侮辱”、“给道德高尚者头顶抹灰”,听起来“义正辞严”,但实际上只是出于根植于潜意识之中的“重义轻利”、“耻于言利”修身理念,对“道不拾遗”、“助人为乐”的“大化之境”的理想推崇,以及对“拾遗近盗”这一“盗心”的深深疑虑,这是一种历史的惯性而不是一种现实的智慧。
事实上,由于法律上并没有确定“拾遗者”获得报酬的权利,我们公安机关“拣拾物品招领处”的生意一日不如一日, 70、80年代这个部门经常收到“交给警察叔叔”的失物,但近十年以来这里已收不到失物了,人们生活节奏加快,捡到东西无利可图不如不捡,搞得不好还要扯上官司(深圳机场拾黄金案),法律的效果实际上大打折扣,现在知道公安局有这么一个专门管理捡拾物品的部门的人,已经不多了。
看到争论中还有法律专业人士言之凿凿地说,“失主向拾金不昧者支付费用是法定的,只不过《物权法》没有像广州这次将比例明确为‘10%’而已”。笔者不得不纠正一下,这种说法确实是对《物权法》的误解,我国《物权法》没有规定向拾得者支付报酬,只是规定了“拾得人有向失主要求支出必要费用的请求权”。在法律上,“费用”和报酬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不能说“费用”就是“报酬”。“费用”是基于无因管理,具有补偿性质;而“报酬”则是对拾得人行为的肯定和奖励,具有表扬性质。
“该不该给拾得遗失物者奖励”是一个法律与道德相冲突的问题。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社会所提倡的道德文明和风尚不能等同法律义务。健康和谐的社会既要求重义轻利的道德观,也要求合法取利的法治观。广州出台“按拾获财物价值的10%的金额奖励拾得者”正是法律与道德一交完美交融,既是道德的法律化,亦是法律对道德的引导。“10%的奖励” 准确地说不是“细化”而是对法律“善良补丁”。非常期望这样的地方性规则成为一种样本,不管是内容亦或形式上的。